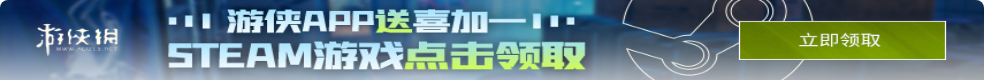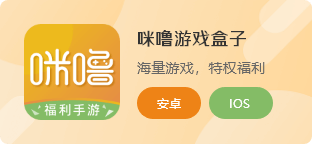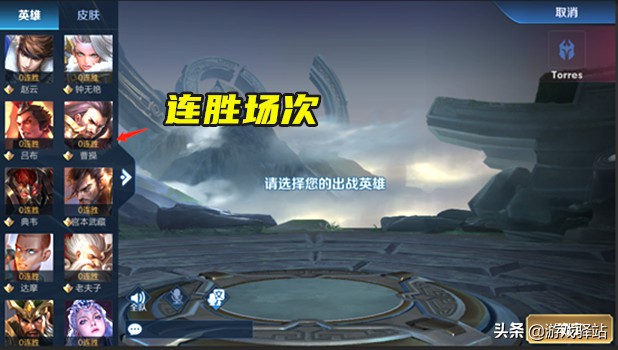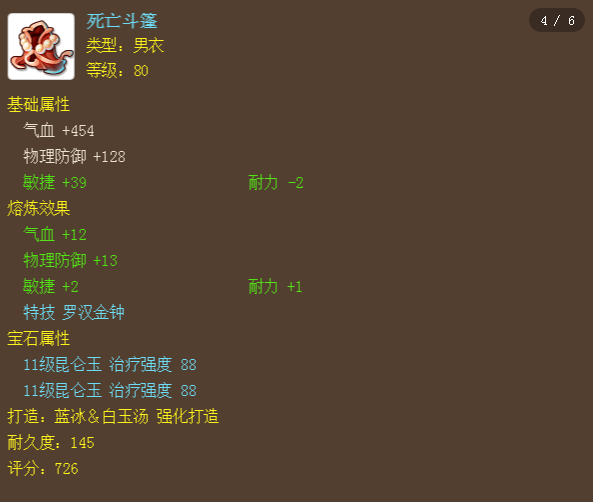当地时间10月21日上午,巴黎市中心的拉桑特监狱门口,59岁的尼古拉·萨科齐提着灰色行李箱迈出车门。箱子里装着家庭照片、三本翻旧的书(其中一本是《基督山伯爵》),还有朋友塞给他的耳塞——这一幕被法国媒体拍下来时,不少人想起五年前他在爱丽舍宫发表就职演讲的样子,只不过今天的他,要走进的是法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前总统的监禁生涯。
拉桑特监狱的名字里藏着个刺眼的反差:法语“La Santé”是“健康”的意思,可这座1867年建成的老建筑,早就是“不健康”的代名词。2000年监狱医生韦罗妮克·瓦瑟尔写的回忆录里,把这儿的状况扒得明明白白:墙壁剥落得能看见里面的砖,霉斑像地图一样爬满墙角,晚上管道里的怪响能吵醒整层楼;老鼠窜得比狱警的脚步声还勤,犯人的皮肤病是“标配”,连自杀率都比巴黎其他监狱高3倍。法国网友编了个段子:“在拉桑特睡觉,你得先和老鼠抢地盘,再和霉味抢呼吸——历史的回声没听见,先听见害虫的叫声。”

但萨科齐不用遭这份罪。他被安排在“脆弱人士区”(其实就是VIP区),9平方米的单人房里有床、桌子和独立洗手池,2014年翻新过的墙面没了霉斑,比普通区“2-4人挤3平方米”的大通铺强出十倍。这儿还能花钱买零食、租电视(虽然只能看法国一台和二台),但萨科齐赛前反复说“不要求特殊待遇”——可光是“不用和其他人挤着睡”,就已经是最实在的“特殊”了。
更让法国舆论炸锅的,是入狱前那趟“爱丽舍宫之行”。10月17日,马克龙秘密会见萨科齐40分钟,直到三天后才被媒体曝光。马克龙在斯洛文尼亚参会时解释是“人道主义举动”,但社会党领袖奥利维尔·福尔直接戳破:“这是在告诉全法国,有些被告比别人高人一等?”法国宪法里“司法独立”是红线,就算是前总统,也不能碰这个规矩——连中间派选民都摇头:“就算是同情,也不该用这种方式。”

萨科齐倒显得“从容”。他第一天就把家庭照片摆上桌子,开始写计划中的新书;放风时抱着《基督山伯爵》,说要“像爱德蒙·唐泰斯那样熬过去”。但外面的世界早乱了:他儿子路易在巴黎豪宅外举着海报喊“爸爸无罪”,支持者举着他的竞选标语围了半条街;极右领袖勒庞之前因挪用公款被禁选5年,现在右翼选民的不满像堆着的干柴,萨科齐的入狱成了火星——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写:“连前总统都逃不过监狱,我们这些普通人呢?”
其实拉桑特监狱本身就是本“法国司法史”。19世纪的德雷福斯蒙冤时,就是从这儿被押去魔鬼岛的;现在萨科齐自称“新德雷福斯”,可历史绕了一圈,变的是犯人的身份,不变的是监狱里的老问题,还有人们对“公平”的质疑——当年德雷福斯的冤案靠舆论反转,现在萨科齐的案子,会不会让法国人重新思考:“法律面前,真的人人平等吗?”

萨科齐的刑期才刚开始。每天1小时的放风时间里,他能看见巴黎的天空吗?监狱的墙皮还在剥落,老鼠还在走廊里窜,可比这些更让人在意的,是法国社会的撕裂——就像那些藏在墙里的霉斑,每露出一点,都让人心惊:原来我们以为的“公平”,其实早有了裂缝。
今晚的拉桑特监狱里,萨科齐会打开《基督山伯爵》吗?没人知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这座“老鼠滋生”的老监狱,会继续见证法国的动荡——就像那些年久失修的管道,每发出一声响,都在提醒人们:有些问题,藏得再久,也会漏出来。